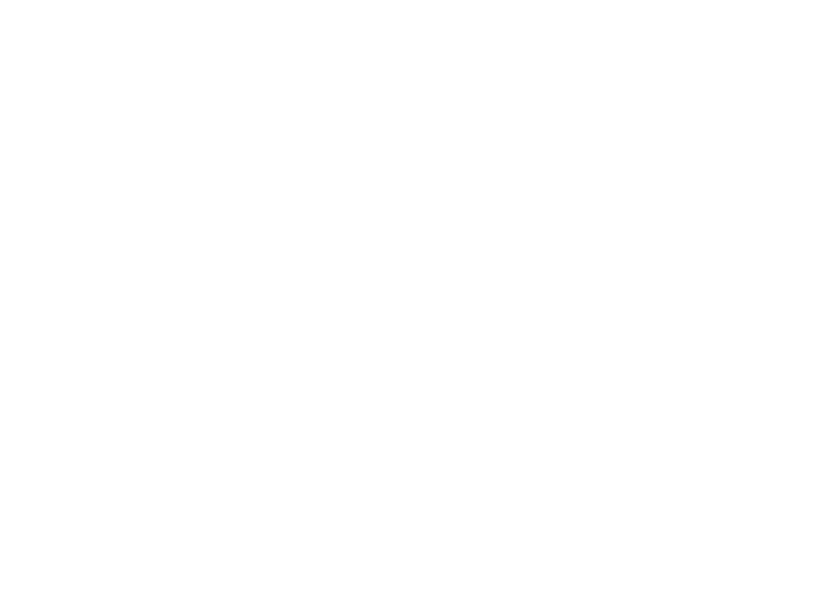“妈妈,我要离家出走,去马戏团当杂技演员。”
我开玩笑,但他没明白。英语不是他的母语,得一个美国人才能理解上下文。对他来说,这是真的。
我不该笑。
“我到那里时你会离开吗?”我问。当时他正在釜山做物理治疗师,我跟他聊天时他正在工作。
他的计划是搬到首尔,然后在亚洲各地旅行,加入各种马戏团练习,最终目标是加入大型马戏团——太阳马戏团或列农兄弟马戏团。
是的。这就是这个家伙的梦想。逃离现实,加入马戏团。
不是当马戏团小丑,而是那些杂技演员,大多是没能进入奥运会的中国或俄罗斯体操运动员。竞争激烈,但他没有放弃。
正是他在约会应用上的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他做手倒立时四肢旋转和伸展的方式让我着迷。
“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想做这个的?”我问。我能看出他是有经验的人,做了很久了。
“我还是个孩子,十岁的时候。我喜欢体操,喜欢倒立,”他说。
“哇。你不晕吗?”我问。
“我喜欢这种感觉。这样站着让我感到平静。”
“那你能用手走路吗?”我问。这些问题确实有点傻,但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,除了那个关于妈妈的玩笑。
“能,”他笑着说。
不该嘲笑别人的热情。“我打算出版我的《Byeontae》书,”我说。
“太好了!你能签名送给我妈妈吗?”他问。
“你认真的吗?你想让我见你妈妈?”我笑了。“那我能问她对儿子跑去马戏团的看法吗?也许我们可以安排一个‘朋友和妈妈’的 spa 日,她可以问我在哪里认识了她 26 岁的儿子。”
“哈哈。他们支持我。”
“我知道。当然。你放弃一份不错的工作来做这个,他们一定很支持你,”我说。
不,我不是在开玩笑。在韩国这样竞争激烈的社会里,一个家庭让儿子做自己想做的事——在马戏团做杂技演员——真是令人惊叹。
我能接受我的孩子这样做吗?
当我和这些男人聊天玩耍时,与对待家人相比,我是否一直有双重标准?是的,双重标准确实存在,但直到我的孩子们长大成人,妈妈还是说了算。
马戏团那家伙对骨骼、肌肉、神经和人体构造了如指掌,我扭伤时曾向他请教过。
在我所处的世界里,这里的职业大多是工程或家庭主妇。我只认识妈妈们,而谈论她们的孩子是我最不想听到的。
这些男人在很多方面都比我有趣得多。他和我在韩国约会应用上认识的许多男人,他们的生活和我或我认识的人完全不同,他们有趣、可爱又性感。
但如果这本书只讲韩国马戏团表演,那就不是《Byeontae》了。
马戏团哥和我彼此匹配,目的只有一个——我喜欢他的腿和手,他喜欢我的胸部。
大胸确实是国际通用货币,能打开所有大门,包括马戏团哥的,因为他就是“胸党”。
是的,他完全符合要求——计划周密、温暖体贴、安全可靠。好吧,也许不是。他可能也是个“屁股控”,但说实话,我不在乎。
他是个受。他喜欢我的霸道性格,喜欢我看他摇晃胸部,用假阳具插入。我们想看视频性爱时就看,我脱光衣服在他工作时给他看,他等着下一个病人。他看了我的Byeontae Instagram照片,我们一起享受了多次高潮和射精。
“你听说过家具色情吗?”我问他。不知为何,想象他双手撑地的姿势让我感到异常兴奋,那些姿势让我想起H给我看的日本色情片。那个类型是我最喜欢的。日本人果然什么色情类型都有。加上他们那古怪疯狂的幽默感,就有了家具色情。
最大的讽刺是,这个想法在我青少年时期也曾闪过脑海。我那扭曲的思维对任何与性相关的事物都充满好奇。
荷尔蒙驱动下,现实世界中的万物都变得像阴茎,随时等待被探索。
我曾幻想整个世界都是阴茎,是一个我渴望尝试的游乐场。
“那是什么?”他问道。
“一个女孩从一张由裸体男人组成的床上醒来,他们都勃起了。她抓住一个阴茎,给他口交,同时揉着眼睛,然后从上到下、从下到上在男人身上滚动。”
“哇,”他回答道。
“是的。太热了!她用一根鸡巴刷牙,挤另一根当‘牙膏’,然后假装另一根是水龙头来漱口。”
“你看到他们的脸了吗?”他问。
“没有。他们戴着连帽面罩。只能看到他们的身体。”
这说得通。要是换作我,我会安排一个脱衣环节,让男人的手慢慢脱掉我的衣服,按摩我的身体,当我弯腰穿裤子时,一个鸡巴插进我的阴道。
想象力可以天马行空。那部家具色情视频相比之下都算温和的,我可以用一屋子的鸡巴玩出更多花样。
“在电影里,她的闺蜜(另外四个日本女人)来探访,每个人都坐在一个有阴茎露出的椅子上,每个女人都被干着,同时聊着日常琐事,还吃着午餐。”
“我明白这个概念,”他说。不过他没有我那么觉得好笑。一个男人跑去马戏团却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好笑的?
马戏团男人不是唯一一个喜欢手倒立的人。还有三个其他人也很擅长手部动作。体操和跑酷在他们那一代人中越来越流行。
我一直好奇,连续不断地移动身体,永不停歇,保持那种持续奔跑的状态,是什么感觉。
我希望自己能像那样。不怕摔倒或骨折。
像他们这样的男人难道有永不枯竭的精力吗?我必须证明这一点,因为实验是我喜欢做的事。
我与那三个男人都发生过关系,除了马戏团男人,结论是,这无关紧要。
在三人中,只有一人有足够的耐力与我玩耍。其余两人在两次高潮后就筋疲力尽了。马戏团男人,我无从得知,因为我们的关系短暂而激烈。
“你有没有想过,做手倒立时口交是什么感觉?”我的好奇心又开始作祟。
“什么?”他的表情符号很生气。
“什么?”我回复道。“你不觉得好奇吗?”
“不!倒立是认真的。”
“当然,我明白。但倒立时你会兴奋吗?”我继续追问。理智已经停摆。我们已经越过了尴尬的界限,进入了危险地带。
我的双脚仿佛在熔岩中沸腾,但固执的思维仍执意前行。
“去你妈的,”他发来短信,瞬间把我拉黑了。
我活该。还是说,我真的值得这样极端的对待?
有时我怀疑自己是否把这个“BRAT”游戏看得太认真了。
谁来惩罚这个调皮的小狗?是你吗?
直到有人阻止我,我都会继续烧毁桥梁。